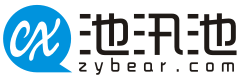设定权利模式是法律保护利益最主要的手段,禁止不正当竞争更多是一种补充机制。法律禁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在广义上属于市场交易主体在商业活动中违反诚实商业习惯的行为。而“违反诚实商业习惯”是一个弹性的概念,裁判者需要在灵活多变的个案中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认定。
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范畴,裁判者亦需要在个案中判断一项到期外观设计是否可以获得反法的保护。在前述“晨光自动笔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对于获得反法保护的到期外观设计需要满足如下条件:(1)使用该设计的商品必须构成知名商品;(2)该设计已经实际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作用,从而可以作为知名商品的特有包装或者装潢;(3)这种设计既不属于由商品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设计,也不属于为实现某种技术效果所必需的设计或者使商品具有实质性价值的设计;(4)他人对该设计的使用会导致相关公众的混淆或者误认。这一规则在2022年3月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反法司法解释》”)中亦有所体现。5
基于此,本文认为对于经过外观专利保护的设计是否可以获得反法的保护,应当遵循以下判断规则。
(一)排除对商品包装、装潢中功能性设计的保护
首先,不论是专门的商标法还是作为补充保护机制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均排除对功能性设计的保护。6中国《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整体或者局部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参照《商标审查审理指南》认为“商品具有实质性价值的形状” 是指“一项使其外观和造型更具美感,从而促使消费者购买该商品的设计”的定义,可知“富有美感”的这一要件的内涵实际上与《反法司法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商品具有实质性价值的形状”一致。那么,若请求保护的商品包装、装潢包含了受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设计,必然意味着该商品包装、装潢是“富有美感”而具有“实质性价值”,从而构成《反法司法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不应获得反法保护的情形。此时,若允许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已经过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设计作为商业标识加以保护,将会导致相关经营主体对功能性设计的垄断,压制同行业之间的公平竞争,最终损害市场竞争秩序,挑战专利法的立法基础。
因此,对于一项到期的外观设计专利,其是否能够作为商品包装、装潢获得反法的保护,必须首先审查其是否构成功能性设计。已有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外观设计专利终止后,该设计并不当然进入公有领域,在该外观设计专利已经实际具有区别产品来源,并且该设计不属于由商品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设计,也不属于为实现某种技术效果所必需的设计或者使商品具有实质性价值的设计,他人对该设计的使用会导致相关公众的混淆或者误认时,该外观设计还可以受到有一定影响的包装、装潢的保护。7这意味着,一项商品的外观设计即使通过长期使用获得了知名度与显著性(具有了一定的商业影响力),但若该设计属于功能性设计,则应当予以排除之后,再讨论其余部分是否可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加以保护。
其次,保护范围应当严格以外观设计作为商品包装、装潢在显著性层面的贡献度为限。
在知识产权领域,公平原则是知识财富分配正义的体现,在制度设计上是对创造者、传播者、使用者三者之间在“垄断利益”和“公有领域利益”的协调,具体体现在:第一,区分知识资源的专有领域与非专有领域;第二,知识产权的独占性与有限性。8具体到本文,若某一商品外观设计在授权期内通过外观专利获得排他性保护,而权利人在此期间通过持续商业推广使该设计积累市场知名度与显著性的,则外观设计专利权对该设计的垄断保护实际上为专利到期后权利人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主张的“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包装、装潢”奠定了排他性使用的基础,即专利制度扮演了“孵化器”的角色:若权利人未申请外观专利,在该设计的进入市场的初期,其他市场竞争者基于合法复制行为将迅速稀释其固有显著性,导致该设计难以积累足够的获得显著性,更不可能获得“有一定影响力”的商誉;正是专利的垄断保护为权利人争取了市场认知培育的时间窗口,使其能够通过差异化竞争建立品牌识别度,从而积累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所必备的“影响力”。
基于专利制度下“垄断换公开”的原则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市场竞争的补充保护定位,专利期限届满后的设计自然进入公有领域,成为社会公众可自由利用的公共知识。正如“晨光自动笔案”中,法院关于“外观设计专利权的终止,至少使社会公众收到了该设计可能已经进入公有领域的信号”的说理——公有领域的设计当然会对有关商品包装、装潢受反法保护时的显著性认定产生影响,至少不应当对有关公有领域的设计的显著性给予过高评价,否则将破坏专利制度“以公开换保护”的立法宗旨以及经营者对专利制度的信赖。因此,在考察商品包装、装潢显著性的过程中,需要权利人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有关设计中的特定装饰性要素(如独特图案、配色、文字布局)通过使用已形成独立于前述设计特征的市场识别性,且被诉不正当竞争主体针对这些要素进行模仿并导致混淆时,方可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加以保护。
综上,经过外观专利保护的设计作为商品的包装、装潢加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时,应当排除对商品包装、装潢中的功能性设计的保护,这是权利人在享受专利法赋予的垄断权时作为对价必须交给社会公众可在专利失效后自由使用的承诺。权利人可以主张反法保护的应当是商品包装、装潢中,独立于前述设计特征且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市场识别性的设计。
(二)严格审查承载有关商品包装、装潢知名度与显著性的设计特征
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法益是市场经营者所享有的竞争性利益,同绝对的财产权存在一定差距。对于这种法益的理解,若作宽泛的解释容易使之实质上滑向专有权的保护,有违禁止不正当竞争制度作为知识产权专门法的有限补充保护的定位。9根据《反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并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的标识,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有一定影响的”标识。因此,如上文所述,权利人将到期的外观设计专利主张反法下商品包装、装潢的保护同样应满足前述对显著性与知名度的要求,即权利人应当提供充分详实的证据证明承载有关商品包装、装潢知名度与显著性的设计特征。
对于知名度的判断,《反法司法解释》第四条提供了指引,即应当综合考虑“中国境内相关公众的知悉程度,商品销售的时间、区域、数额和对象,宣传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域范围,标识受保护的情况”等因素。
而对于显著性的判断,尤其是对于商品形状类的包装、装潢的显著性判断,往往是实践中的难点。最高人民法院在前述“晨光自动笔案”中曾提及原因,“形状构造本身与商品本体不可分割,相关公众往往更容易将其视作商品本体的组成部分,而一般不会直接将其与商品的特定生产者、提供者联系起来。”因此,对于一项原本作为外观专利加以保护的设计,其作为商品包装、装潢是否具备显著性的判断,应当以更严格的条件加以审视:(1)该形状构造应该具有区别于一般常见设计的显著特征;(2)通过在市场上的长期使用,相关公众已经将该形状构造与特定生产者、提供者联系起来。基于前文所述,这需要权利人提供证据证明使相关公众将有关商品包装、装潢与权利人相关联的要素恰好是独立于商品包装、装潢中的功能性设计且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市场识别性的设计,不应简单粗暴地根据销售额及投放成本的堆砌集合,便笼统认定权利人受反法保护的商品包装、装潢权益及于其商品整体。
(三)区分近似性与混淆可能性的判断标准
在设权模式之下,外观专利权保护的是权利人对外观设计排他性的使用权;在禁止不正当竞争模式下,反法保护的是商品包装、装潢所承载的商业上的竞争利益。设权模式和禁止不正当竞争模式对权利人权益保护模式上的差别,体现在《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商品外观设计保护模式的差异即为:在适用条件上,《商标法》作为权利保护法,其适用条件比作为行为规制法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更加宽松。10即,《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品包装装潢在内的商业标识的补充保护没有理由强于对注册商标的保护。举重以明轻,如在个案中,权利人主张保护的包装装潢相同要素注册的商标被认定为不足以得到商标专用权保护,那么其主张反法下的商品包装装潢权益,则更缺乏正当性。11
相应地,对于外观设计专利权侵权和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规则也存在差异。前者为从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出发,比对授权外观设计与被诉侵权设计的所有特征,进而判断二者是否相同或近似;后者则从商品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出发,隔离比对权利人主张的“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包装、装潢”和被诉侵权商品包装、装潢的相应特征,结合主张权利的商品包装、装潢的知名度与显著性,判断二者是否容易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即最终落脚点是被诉包装、装潢是否容易使相关公众认为其与权利人存在特定联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现代知识产权法坚持保护权利人的底线,而现代反不正当竞争法则以经营者、消费者和公众利益的三元保护为目标……反不正当竞争法从不禁止一切对在先知识产权的模仿行为,而是规制那些具有不正当性的仿冒方式。”12即,单纯的模仿并不必然造成混淆,更谈不上“不正当”。相似性为造成混淆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混淆可能性才是责任成立的核心。
因此,对于经过外观专利保护的设计是否能够给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的判断标准,并非设权模式下的“近似标准”,而应当在构成近似的前提下进一步考察被诉设计与主张保护的设计是否会导致相关公众的混淆。混淆可能性需要结合包装或装潢承载显著性的部分、其与被诉包装或装潢是否近似、商品的属性、市场环境、消费者存在被误导商品来源的初步证据、与权利人主张保护的包装或装潢相同要素注册的商标受保护的记录等多维度因素进行判断,避免机械适用“相似即侵权”的规则,以平衡权利保护与市场竞争自由。